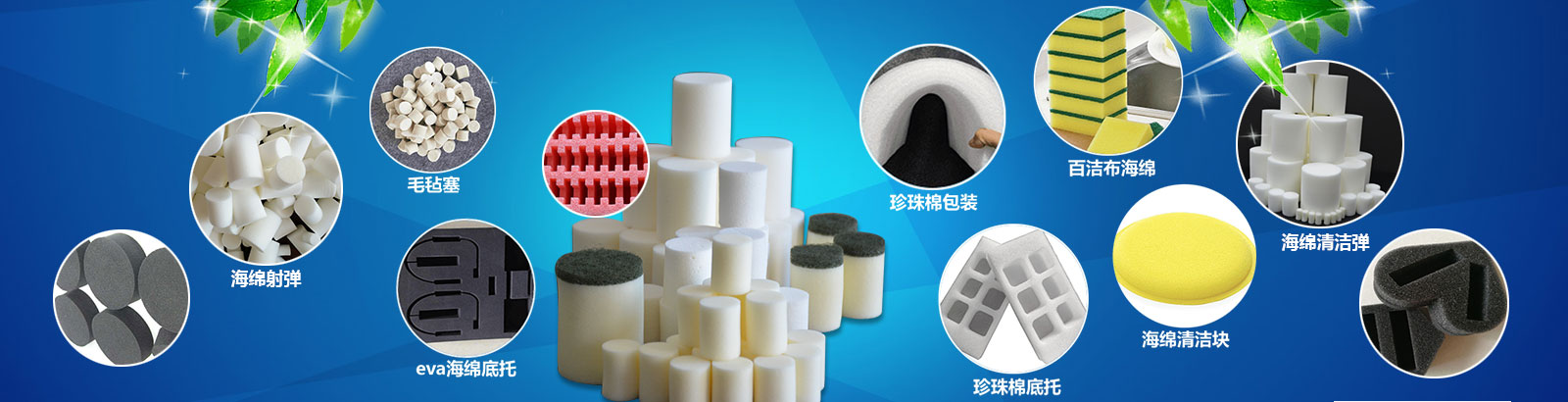14岁少女被男同学邀请去公园后失踪两名未成年凶手镇静应对谎言百出
时间: 2024-12-08 09:08:18 | 作者: 小九直播官网app下载

“命案列国志”是没药花园拟推出的新系列,旨在通过集中审视发生在某个国家的多起命案,呈现出该国的历
“命案列国志”是没药花园拟推出的新系列,旨在通过集中审视发生在某个国家的多起命案,呈现出该国的历史、文化、经济、国民性等情况,以及这些社会因素对案情和对当事人命运的影响。本系列的作者斯温将重点介绍中文网络中鲜少介绍过的案件。
爱尔兰,偏居欧洲西北一隅,只有英国一个邻国,在地理政治学中属于边缘的边缘。该国面积不大,人口不多,地处高纬度地区,又受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天气多变,多风多雨。爱尔兰土地贫瘠,资源匮乏,在历史上长期处在欧洲穷国行列,曾被英国统治多年。
从上世纪90年代起,爱尔兰全力发展高科技、制药、金融等产业,凭借低税率的优势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创造了号称“凯尔特之虎”的经济腾飞期,一跃变成全球最富国之一,远超于了曾经的宗主国英国。2023年,爱尔兰的人均GDP超过11万美元,仅次于卢森堡,排名世界第二。笔者旅行时发现,从英国境内的北爱尔兰进入爱尔兰境内后,基础设施的水平和手机信号的强度都提高了不少。
爱尔兰总体治安情况还算不错。近几十年发生的凶杀案件中,有一多半与爱尔兰共和军(IRA)有关,剩下一小半里,又有一多半与黑帮火并有关。这两类案件都有特定的对象,前者是政治人物,后者是帮派分子。普通老百姓正常情况下不会受到影响。
但是,经济再发达、治安再好的地方,也无法逃脱恶性案件的发生。本文所述的案件当中,两位年仅13岁的罪犯在作案过程中表现出的冷酷和残忍,以及面对警方调查时的“成熟”和“冷静”,都能让人深切地感受到阳光下潜伏的人性之恶。本案中暴露出的一些司法问题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近些年来,伴随着经济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大量外国移民涌入爱尔兰,改变了这里较为单一的人口结构和简单的社会关系。21世纪以来,爱尔兰的多起重大案件均与移民群体有关。他们之中既有犯罪者,也有受害者。本案中的受害者安娜就是一位14岁的移民少女。
安娜克里格(Ana Krigel)2004年生于俄罗斯的新库兹涅茨克市,出生后不久就被送进了孤儿院。两年后,来自爱尔兰的克里格夫妇(Geraldine and Patric Krigel)收养了安娜,把她带回爱尔兰,住在首都都柏林郊外的卢坎镇。
不知道安娜是不是因为健康原因而被亲生父母遗弃的,总之,她从小就被一些健康问题所困扰。她的右耳长了一个肿瘤,后来做了五个半小时的手术才切除,但手术后那只耳朵几乎完全丧失了听力,头上也留下了一个大伤疤。此外,她的视力也有很严重的问题。
身体的缺陷,加上外国领养的身份,让安娜成为了同学们霸凌的对象。到了小学高年级的时候,她就出现了心理问题,甚至有自杀倾向。进入中学后,安娜遭受的霸凌更严重了。来自西伯利亚的她从小就比同龄人高大很多,13岁时已长到1米73,看起来像成年人一样,这使得来自男生的霸凌之中又多了一些性骚扰的成分。
安娜曾跟养父母说过,她渴望交朋友,但在学校却总是形单影只,像个隐身人一样。大多数时间,她都只能戴着厚厚的耳机在校园里独自徘徊。有一次,她上学前把自己的一只眼睛画成了黑色,养父母认为那就是她想要引起别人注意的表现。
悲剧发生在2018年5月14日,星期一。这一天,安娜上午在学校上课,下午请假去见自己的心理咨询师,之后回家。4点55分,安娜家的门铃响了,养父帕特里克去开了门。来人自称小勇。(为保护未成年人隐私,爱尔兰警方和法院始终未公布两位嫌疑人的姓名。媒体称其为‘男孩A’和‘男孩B’。为叙述方便,本文将‘男孩A’称为‘小亮’,‘男孩B’称为‘小勇’。)安娜听到这一个名字很疑惑,她知道有小勇这么一个人,但两人绝对称不上是朋友。不过,她还是下楼见了小勇。
帕特里克看到安娜在门口和小勇说话,但声音很小,完全听不见。他也没感觉出有什么异样。接着,他就看到安娜上楼抓起一件连帽衫,跟那个男孩出去了。这件连帽衫是黑色的,袖子上有显眼的白色图案。帕特里克没想到,几天之后,安娜穿着这件衣服的照片出现在了爱尔兰几乎所有报纸和电视画面之中。
安娜临出门时,帕特里克曾提醒她,明天还有考试,今晚应该在家复习。但是,安娜说她不会出去很久。“我相信她当时说的是真话。”帕特里克后来说。他回忆说,安娜出门的时候很开心。
然而,安娜刚走,帕特里克就发现了自己忘了问她要去哪儿。他走到门口,看到安娜朝着镇上的圣凯瑟琳公园方向走去了,小勇则走在她的前面。两人似乎没有交谈。
5点10分,安娜的养母杰拉尔丁在下班途中给安娜打了个电话,但安娜没接。杰拉尔丁到家后,得知安娜和一个叫小勇的男孩出去了,立刻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因为安娜根本就没几个朋友,“从来没有人来找过她”。
5点半,杰拉尔丁给安娜发了一条只有两个单词的短信“马上回家(Home now)”,几分钟后又发了一条:“不回复我就报警了”,但还是没有回音。她步行去圣凯瑟琳公园寻找安娜,也没找到。回家后,她又和丈夫一起在脸书网站上查找小勇的完整姓名。他们两个人以前对这一个孩子有一点印象,但是不知道他住在哪,也不认识他的父母。然而,网上的搜索也没有正真获得什么结果。
在一位朋友的建议下,夫妇两人来到警察局报警。这时距离安娜离开家已逝去了四个小时。在家长看来,四个小时已经长得让人发疯了,但对于警察来说,这点时间还不符合“失踪”的标准,毕竟他们每周都会收到至少几十个儿童失踪的报警,但这一些孩子绝大部分都会在几小时内被找到。于是,杰拉尔丁竭力向警察解释,安娜从来不会不接电话、不回短信,而且出门前也没吃晚饭、没带证件。这些都说明她的失联很不正常。
杰拉尔丁的劝说起了作用,警方决定采取行动。他们通过警局内部系统找到了小勇的住址,并派了一位警官来到小勇家,发现小勇就在家里。他对警察说,自己确实和安娜一起去了公园,但5点40分就先行回家了。
安娜一夜未归。第二天早上,警方也开始担忧起来,真正开始启动了失踪人口调查程序,并通过媒体发出了寻人启事,其中就包括安娜穿着黑色连帽衫的那张照片。同时,另一位级别更高的警官约翰邓恩(John Dunne)来到小勇家,再次向他了解情况。这一次,小勇第一次说出了小亮的名字。
小勇说,昨天他是替小亮把安娜叫出来的。安娜暗恋小亮,但小亮对她不感兴趣,就想把她叫出来当面说清楚。小勇把安娜带到公园,见到了小亮,然后自己就回家了,后面发生了什么他也不知道。
邓恩警官把小勇带到公园,让小勇指出他和安娜进入公园、见到小亮,以及离开两人时的具置,然后就放小勇回家了。邓恩自己又在公园附近寻找线索,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带着孩子的男子。那名男子说,他已经看到了寻人启事,并建议邓恩到废水处理厂的后面找一找,因为他经常看见中学生在那一带活动。
当天晚些时候邓恩才知道,他遇到的这名男子就是小亮的父亲,他带着的那个孩子就是小亮。
直到此时,警方都没有把两个男孩视为嫌疑人,只是觉得他们两个是最后见到安娜的人,想从他们身上得到线索。于是,警方把小勇和小亮一起叫回了公园,让他们再确认一遍昨天的见面地点。这一次邓恩察觉出了异样:小勇带的路和早上不一样了;而且,在一个小轮车(一种自行车类的体育项目)场附近,两名男孩明显在用眼神交流,好像是在商量下一步往哪条路上走。
小勇的证词和前一天晚上没什么区别。小亮的证词则更详细一些,不过跟小勇的证词并不一致:他说自己是让小勇去公园找他,等小勇到了才发现安娜也来了。他在学校认识安娜,但并不熟。
对于两人见面后的事情,小亮是这样说的:聊了几句后,安娜突然问他“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愿不愿意跟我约会?”把他吓了一跳。不过他又说:“我隐隐约约知道她喜欢我,因为她以前也类似这样地问过。”接着,他“委婉地”拒绝了安娜,而安娜什么也没说,带着生气和难过的表情走开了。
小亮的证词继续:由于小勇早就走了,此时只剩下了他一个人。不久,他遇到了两个男人的攻击,其中一个人抓住他的肩膀把他按在地上,然后两人一起踢他。小亮奋力站起身,然后踢中了其中一人的头部,两人才跑掉了。小亮此后回了家。
听到这番话,警官又仔细检查了一番小亮的身上,确实有打斗的痕迹。他的胳膊和腿都受伤了,脸上也有抓痕。但是,警方还是感觉这一个故事有哪里不对。尤其是,两个人都站着时“踢中了对方的头部”这个细节,在实际的打斗过程中是很少发生的,听起来更像是少年人的一种想象。
警方还是向小亮询问了两名攻击者的外貌特征,小亮也煞有介事地进行了一番描述。但是,无论是案发时在公园内的证人,还是公园各处的摄像头,都未曾发现任何符合描述的嫌疑人。
安娜是5月14日傍晚失踪的,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5月16日。此时,警方严重怀疑安娜已经遭遇不测。他们动员了更多警力,扩大了范围,对公园及附近地区展开网格式的大搜索。
5月17日晨,警方的一个四人搜索小组结束了对公园内一大片草地的搜索,来到紧邻公园边界的格林伍德府。这是卢坎镇上一座废弃的农场建筑,建于1800年,案发时已经有几十年没人居住了,破烂不堪,变成了一些“不良少年”聚会玩乐的场所。
搜索队员进入楼内。在走廊尽头的一个房间,一位警员向屋里看去。由于窗户被封住了,屋里一片漆黑,但这位警员隐约觉得看到了一个人形,然后立刻就闻到了血液凝固后的味道。走进屋内后,他确认那个躺在地上的人形就是早已没有生命迹象的安娜。她全身赤裸,只有袜子还穿在腿上。头发几乎完全遮住了脸。安娜的身上有多处伤口,脖子上缠着厚厚的绝缘胶带。她的三根手指还在胶带里面,似乎是在试图解开脖子上的胶带。
房间里散落着安娜的衣服和手机,墙上和地毯上都有血迹,还有两样沾满血迹的物品:一大块水泥和一根木棒。她戴的假指甲掉了一地,显示出她可能与凶手进行过殊死搏斗。现场并未曾发现除安娜之外的指纹和血迹,但法医在她的胸罩上发现了精斑。
当晚的尸检显示,安娜的身上共有50处伤口,全身上下都布满了淤青和擦伤痕迹。伤势最严重的部位是头部、面部和颈部。医生判断致命伤来自头部和颈部遭受的钝器打击。同时,安娜的脖子上也有勒痕,但不确定是不是那捆胶带造成的。她的也遭到了侵犯。
根据现场勘察和尸检的发现,警方推测出了安娜死前的经历:她进屋后先是被那根沉重的木棒打倒在地,然后又被水泥块击打了四下。接着,她可能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被拖到窗边并遭到。
警方的调查重点立刻转回到了那两位男孩身上,因为当地的警察都知道格林伍德府是中学生经常出没的地方,而且两人的证词本就疑点丛生。之前在小亮供述自己遭到两名男子的袭击时,警方拿走了他当时穿的鞋去化验。几天之后,法医在这双鞋上发现了安娜的血迹。
在小亮的手机里,警方发现了其他的可疑迹象:他相册里有多张重口味的视频截图,包括“史上最残酷的15种酷刑”“脱掉杰西卡的衣服”“杀手杰夫”等等。他的搜索记录里也有一条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卢坎镇的废弃场所”。
安娜的尸体被发现一周后,两名少年被警方逮捕。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两名男孩开始了令人震惊的“精彩”表演。
首次面对警方正式讯问的小亮显得镇定而成熟。在被问到个人兴趣的时候,他坦然回答“解剖学、人体”,还喜欢绘制解剖图。
警方给小亮看了公园里的监控录像。他指着画面里的两个人说,这两个人好像就是“袭击”他的人,还问警察说:“这可能是个好消息(能证明他与安娜分开后被两个人袭击的故事),还有别的画面吗?”实际上,画面里的那两个人是小勇和安娜。
接着,警官告诉小亮,他们已在小亮的鞋上发现了安娜的血迹。小亮一脸无辜地答道:“你是在搞笑吗?”警官严肃地说:“告诉你,你鞋上的血迹只可能是在一个地方沾上的,那就是安娜被杀害的那个房间。所以我再问你一遍:你去过那个房间没有?”
面对警方给出的其他证据,小亮也一一否认:他没见过缠在安娜脖子上的胶带,手机里的“酷刑”搜索记录则是自己在找恐怖片的时候留下的。至于其他证据,他的回答基本都是“不知道”“没什么可说的”。
面对这样一个“小屁孩”,经验比较丰富的警方竟然束手无策,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对小勇的讯问能率先取得突破。此时他正在几公里外的另一个警察局接受讯问。
然而,似乎处于“从犯”位置的小勇,在与警方的较量中的表现丝毫不“逊色”于小亮。
起初,他仍然坚持自己把安娜带到公园后就离开了。警方当场播放了公园各处的监控录像,显示出小勇根本就没再次出现在他所描述的路线上,但小勇还是坚持自己的说法。双方就这样僵持了一天。
按照爱尔兰法律的规定,警方不得将未成年的嫌疑犯关进看守所。于是,到了晚上,警方在警察局临时搭了一张床,让小勇和他的母亲在办公的地方里过夜(按照法律规定,未成年人接受讯问时必须有监护人在场)。第二天早上,小勇的口供第一次出现了松动:“昨天我说的都是假的,现在我要把真实情况重新讲一遍。”
不过,他所说的“真实情况”让警方大失所望:他只是把自己和小勇在公园里见面的地点从大路边改成了小轮车场,其他证词一点都没变。之后,随着警方不断出示新证据,小勇又陆续改变了几处说法,但始终避重就轻,否认自己明白发生在格林伍德府的任何事情。
参与审讯的警官都受过专门的训练,掌握各种给嫌疑人施加压力的技巧,但是在与小勇的“交锋”中,他们从始至终保持着温和的态度,因为对未成年嫌疑人的任何鲁莽言语将来都可能在法庭上被质疑为“威胁”或“诱供”,因此导致口供失效。
问题是,眼前的这位未成年人比成年人还难对付:他思维敏捷,表达清晰,且拥有着远超一般初中生的词汇量——他能准确地分辨“拘留”、“逮捕”、“谋杀”等概念,甚至在描述安娜的穿着时用了“合成皮革”(synthetic leather)这样的词汇。尽管已经在两天内接受了近10个小时的高强度审问,但这位年仅13岁的孩子从始至终保持着冷静,就没有流露出任何情绪。
到了第五轮讯问时,警官多纳尔达利(Donal Daly)先绷不住了,他已经受够了小勇无尽的谎言。“有一个女孩被残忍地杀害了,你欠这里所有的人一个真相,欠你的母亲一个真相。” 他用严肃的语气对小勇说,“从开始到现在,你一直在不停地撒谎,我们出示一个证据,你就新编一套说辞,你不能再这样了。”
这番话起了作用。小勇沉默良久,然后要求她的母亲离开审讯室。达利拒绝了,他担心监护人不在场时录得的口供被法庭拒绝。小勇的母亲见状提议休息一会儿,但达利再次拒绝。
小勇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说出了一个新的故事:小亮带着安娜走进了格林伍德府,他跟在后面,但没有进去,然后就听到里面传来尖叫声。“那声音很刺耳,我知道是安娜在叫,但我想小亮在里面,他会保护安娜的。过了一会,尖叫声就停了,好像是她的嘴被捂住了。”他吓坏了,就转身回了家。
虽然这仍然是谎言,但小勇总算在撒了无数次谎之后,第一次承认自己明白安娜被小亮带进了格林伍德府。说完之后,他留下了眼泪。
心理防线被突破之后,小勇开始挤牙膏似地说出更多的真相。没过多久,他就承认自己并没有离开,而是在小亮和安娜之后也走进了格林伍德府。他听到走廊尽头的房间里有动静,就跑过去查看,发现小亮掐住了安娜,并开始脱她的衣服。安娜则一边哭一边求饶。接着,两个人都发现了站在门口的小勇。小勇一慌,就跑开了,不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事后证明,这番话仍有所隐瞒,但在法律规定的留置时间之内,警方虽又进行了两轮讯问(一共七轮),但没能再取得什么突破。
与此同时,警方火速把小勇在第五次讯问中透露出的“真相”打印出来,去找小亮对质。小亮看了以后轻描淡写地说道“他说谎”,然后就不置一词。24小时的留置时间眼看就要到了,恰在此时,警方得到了检察官的通知,准许他们以谋杀罪名起诉小亮。法官要求将小亮转移至一处专门关押未成年嫌疑人的拘留所,且不得保释。
随后,警方对小亮家进行了搜查,在他的房间里发现了一个被警员称为“杀人套装”的背包,里面装有手套、护膝、护腿板、束发带,以及一个自制的骷髅面具。除了护腿板以外,上述物件和背包中全都验出了安娜的血迹。其中手套的作用至关重要:正是因为它,现场才没有留下小亮的指纹。这也说明他对这次谋杀早有准备。最后一个关键证据是,安娜内衣上的精斑和小亮的DNA相符。
掌握这些证据后,达利再次对小勇进行了讯问。这一次小勇又说出了与前几次不一样的故事:他不是在安娜和小亮后面进的房子,而是先进去的,那根木棒也是他找到的。他还看到小亮在攻击安娜时戴着那个骷髅面具。那是小亮在前一年的万圣节做的,小勇觉得“非常酷”。不过,他仍然否认自己参与了攻击。
小勇还说,小亮在事发前的一个月就跟他透露了谋杀安娜的想法,但他当时认为小亮只是随口说说而已,并不知道对方真的在计划此事。案发时,他自己也被吓傻了,因此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随后对警方不断撒谎则是因为“想赶紧忘掉这件事,假装它没发生”。
这一次,达利毫不客气地说:“是你把安娜叫出来,亲手交到了小亮的手上,而你早就知道小亮有杀掉她的想法。你只是在不停地撒谎,对每一个人撒谎。”
在爱尔兰,凶杀案从逮捕嫌疑人到开庭审理,通常都需要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像这种证人证据都很多的案件往往会拖上更久。但是这一次,或许是因为两名少年的罪行太令人发指,与案件相关的各个机构不约而同地开足了马力,甚至有很多人自愿加班工作。最终,庭审于2019年4月开始,距案发不到一年。
按照爱尔兰法律的规定,年满12周岁就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如果是杀人或案,这个年限还会下调到10岁。小勇和小亮案发时都是13岁,他们成为了这一个国家历史上被诉以谋杀罪名的最年轻的被告。案件的审理受到了全国的高度关注。
除了身份信息被严格保密外,未成年人在法庭上也享有一些“特权”:他们能够从法院的侧门进入,在休庭时也有独立的休息室,由此避开媒体和公众的视线;庭审过程不对外开放,只有五名记者被允许入内,但法官警告他们:泄露被告人的任何信息都会被视为犯罪;被告人可以不坐在被告席,而是和家人一起坐在旁听席。在庭审过程中,两名被告显露出了孩子气的一面:小亮经常把头靠在父亲的肩上,而小勇则几乎全程都握着母亲的手。
由于证人证言众多,法庭的审理过程持续了七周。两名少年的父母,以及安娜的养父母全都作为证人出庭,但他们的表现都很理性:前者没有为自己的儿子喊冤,后者也没有情绪失控或辱骂嫌疑人。
两名被告的律师对大部分证人都没有发问,但他们偶尔提出的问题显露出了不同的辩护策略。小亮的律师问安娜养母的问题是:安娜是否有性经验?安娜的养母回答没有,随后出示的医学证据也证明了这一点。
随后,小亮的律师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了质疑证据上,因为此案中有大量的证据对小亮不利。他提出,那双沾有安娜血迹的鞋应被排除,因为警方是以调查小亮“遇袭”为名获得这些证据的,取证方式不当。对此,当时拿走那双鞋的警官表示,她当时并非有意欺诈,而确实在调查小亮“遇袭”的案件,甚至都不知道安娜已经死了。法官接受了她的解释,认为证据是有效的。
接着,律师又提出DNA检测结果也应排除,因为警方在填检验单的时候,填错了单子。法官认为这样的一个问题并不影响检测结果的真实性,因此对这一要求也予以驳回。这样,对小亮定罪起关键作用的物证就都被采纳了。
小勇的情况则完全不同:没有一点物证对他不利,但他在录口供的过程中屡次撒谎的行为无疑令法官和陪审团的“印象分”大减。因此,律师主要的工作就是为他的撒谎行为做出辩解。律师对参与讯问的两位警官提出了大量问题,试图找出他们在执法程序和行为上的纰漏,但并没什么收获。
小勇的律师还请来了一位心理学专家。他在为小勇做鉴定并听了警察局的讯问录音后表示,小勇之所以多次撒谎,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所致,因为他在目睹安娜被攻击后受到了刺激。这位专家说,他认为小勇事先确实不知道小亮的杀人计划。
对这个结论,公诉人提出了强烈的反对,认为“小勇是否事先了解这一个计划”应该交给陪审团去判断,而专家的“结论”会起到误导作用。法官在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后,宣布拒绝采纳这位专家的所有证词。
公诉人提出的证据也有很多没被采纳,包括在两位少年家中和手机里找出的恐怖片、色情影像、搜索记录等等。法官认为这些记录与谋杀没有直接关系。
在整个庭审过程中,两名少年始终拒绝认罪,小亮甚至不承认自己到过谋杀现场。用公诉人的话说就是“一个孩子明明嘴里塞满了巧克力,却还说自己没吃”。
但是,由于现场有大量与小亮有关的物证,他的律师在最后近一个小时的总结陈词中,并没有试图证明小亮与安娜的死无关(但也没有明确承认有关)。他的发言主要围绕两点:第一,没有证据说明小亮有杀人的预谋——“小亮说过想杀死安娜”只是小勇一个人的说法,无另外的人能证明,而且即使小亮这样说过,也很可能只是开个玩笑。
爱尔兰的法律将杀人罪名分为两种——非预谋杀人(manslaughter,包括激情杀人和过失杀人)和谋杀(murder),两者的量刑是不一样的。小亮被起诉的罪名之一是谋杀。律师的主要诉求就是让陪审团同时考虑这两个罪名,但遭到了法官的拒绝。
小亮律师的第二个观点是:小亮被起诉的另一个罪名——性侵——不成立。他表示,小亮和安娜可能是自愿发生性行为的,没有证据说明存在强迫行为。
小勇的律师则为他的谋杀罪名做了无罪辩护,认为安娜的死完全是小亮一个人的责任。律师仍然把重点放在“小勇不知情”这个点上。他说,如果小勇知道小亮真的要杀死安娜,他就不会傻到在沿路众多摄像头下上门叫走安娜,并把她带到公园。同时,虽然心理学专家的证词没被采纳,但律师仍坚持说小勇撒谎是因为受到了刺激。
没有证据说明小勇参与了小亮对安娜的性侵和杀害过程。法官告诉陪审团,在谋杀发生时在场,或者没有阻止谋杀,都不是犯罪。所以,核心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小勇在叫走安娜的过程中,是否清楚自己在执行小亮的谋杀计划——或者说,在事发前一个月听到小亮说要杀死安娜的时候,小勇是否认为他是认真的。这一点没有一点证据能直接证明,只能靠陪审团去判断。
这时,小勇在庭审过程中曾说过的几句话引起了陪审团的注意。他说安娜是一个“怪咖”,没人愿意跟她一起玩,还说她经常“衣着,千方百计地想引起男生的注意”。陪审团认为,这几句话表明小勇知道小亮要对安娜做什么。
陪审团的讨论持续了五天,总计接近15个小时。2019年6月18日,12名陪审团成员都同意判定小亮的谋杀和性侵罪名成立,小勇的谋杀罪名也成立。全场沉默了半分钟后,小亮在父母的怀里哭了起来,小勇则双手捂头。
小亮的家长或许是早有心理上的准备,在听到结果后并没有说什么。安娜的养父母也没有说话,只是向陪审团点头致意。只有小勇的父亲激动地猛砸法庭的门,并高声叫骂起来:“你们这群混蛋!小人!我儿子是无辜的!”
在被带离法庭的时候,小勇回过头问自己的妈妈:“我会和他(小亮)关在一间牢房里吗?我不想见到他。”在此前长达七周的庭审中,在场的记者观察道,两位少年自始至终没有一点互动,连眼神交流都没有过。
几个月后,法官宣布判处小亮无期徒刑(爱尔兰没有死刑),12年内不得减刑;小勇有期徒刑15年,8年内不得减刑。之后,小勇的家人提起上诉,但未获成功。
在宣判前,法官曾安排医生给两名身处看守所的少年做精神鉴定。或许是为了争取较轻的刑罚,小亮此时终于承认自己杀死了安娜,但仍否认性侵罪名。小勇则坚持表明了自己无罪。
此案的余波并未平息。众多爱尔兰民众对保护未成年人隐私的法律提出了质疑:为何司法机构需要极尽各种措施保护两名少年凶手的身份?其中一些“意难平”者甚至自己采取了行动。
2019年6月19日,也就是两位少年被裁定有罪后的第二天,一位名叫利安达法雷利(Leeanda Farrelly)的都柏林市民在一个有2万多名用户的Facebook群组里上传了小亮的照片,并留言呼吁网络上的朋友转发:
“就是这两个(实际上她只上传了小亮的照片)杀害了那个可怜的小女孩……把他们邪恶的脸转发起来吧,他们以后会改名换姓的。”
20分钟后,法雷利在家人和朋友的劝说下撤下了照片,但这起事件仍然引起了警方的注意。2024年6月19日,法雷利被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但缓期执行。
违反禁令的不止法雷利一个人。截至2024年11月,至少还有三个人因为在社会化媒体上传播小亮和小勇的照片而遭到起诉。他们的案件仍在审理之中。
参与了庭审的那几名记者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拐弯抹角地写出了一些小亮和小勇的真实信息,而这一些信息又引发了更多的追问。
这些记者在报道中写到,这两个孩子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问题少年”:他们都出身于幸福和睦的中产家庭,有着良好的教养,不碰烟酒,也从来没有一点不良纪录。那个谎话连篇的小勇甚至是一个“不学习还总能考第一”的高智商学生。那么,到底是什么驱使年仅13岁的小孩犯下如此骇人听闻的罪行呢?
2023年,也就是案发五年后,小勇的父母第一次接受了媒体的采访。他们说自己为安娜的遭遇感到万分难过,并责怪小勇没有出手阻止小亮行凶,但坚持认为小勇不能算是凶手之一。